杀死曹爽的不是愚蠢,而是软肋
曹爽用一句话夺去了太尉司马懿的兵权,在其后的十年里将司马懿稳稳压制,无论是凭他自己的脑子还是听取了智囊团的建议,作为领袖的曹爽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蠢人。

演义中《司马懿谋杀曹爽》一回的时间跨度极大:开头曹叡去世,司马懿、曹爽开始辅政,发生在239年;结尾曹爽请曹芳去高平陵祭祀,司马懿开始动手,发生在249年。
十年前,曹爽每天与何晏等人喝酒。十年后,曹爽每天与何晏等人喝酒。这十年中天下发生的一切事件,作者都略去没写。他只写了一件事,就是管辂给何晏等人看相,看出了个大凶之相。
作为上了演义回目的第一神棍,管辂的预言无疑百发百中,但是何晏长成这个相貌不是一天两天,何以十年前就平安无事,十年后突然有血光之灾?对这十年作者没写下任何一个字,发生了变化的究竟是什么?
情节中只发生了一件事:曹爽喝酒喝腻了,于是兴趣转向打猎。
曹爽虽然奢侈无度,但是对兵权的掌握非常牢固。他在京城自己府里喝酒,只要人不离开京城,局面就稳如泰山。可打猎这种兴趣,本人要离开京城。

弟弟曹羲、智囊桓范看出了潜在的风险向曹爽进谏,但是曹爽语言托大。爪牙何晏劝曹爽留意养病的司马懿,曹爽嘴上不屑一顾,但派了李胜去刺探情报。
李胜带回来的结果十分喜人,听知司马懿命不久矣的曹爽大喜过望。从这里的大喜可以看出,曹爽直到这时对司马懿仍有提防。十年来司马懿的蛰伏虽然让曹爽麻痹大意,但那根神经始终没有完全松下来,到这个时候,才完全松下来了。
这就是演义中着重写司马懿装病情节的原因。十年中的蛰伏只造成了曹爽心态的量变,虽然从在家喝酒变成外出打猎,但京城兵权始终在曹氏兄弟手中。十年后的表演对曹爽的心态来说才是质变,此后他敢于带走所有的弟弟一起外出了。在他们外出的时间窗口里,京城的兵权处于真空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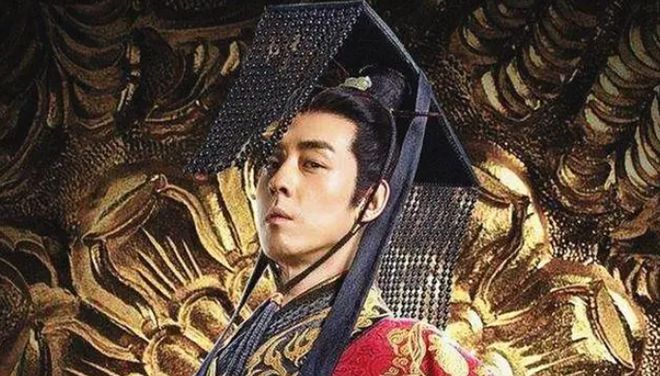
全书智谋仅次于诸葛亮的第二谋士司马懿,用十年时间等到了这个机会。
二十年前,洛阳城没有收到司马懿的请示报告,他已经动若飞星直取孟达。二十年后,司马懿让洛阳城亲眼看到了什么叫兵贵神速。在曹爽出城的当天,司马懿就展开了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京城的军事力量,并亲自入宫威逼太后拿到了政治合法性,在蒋济和司马孚写表诬陷曹爽谋反的同时,司马懿亲自带兵驻守洛阳浮桥。
整整十年的其徐如林,几个小时的其疾如风。十年来曹爽只给了司马懿这一个机会,司马懿毫不犹豫地抓住了它。
但曹爽到这时都还没输,因为桓范带着大司马印赶来了。
作为曹爽集团的智商担当,桓范的脱逃让司马懿大惊失色,司马懿知道曹爽仍有胜机,只要听了桓范的建议移驾许都,鹿死谁手就仍有悬念。但蒋济用一句话打消了司马懿的不安。
蒋济曰:“驽马恋栈豆,必不能用也。”
于是司马懿竭尽全力让曹爽相信自己只想夺权并不害命。这是围师遗阙的基本原理,司马懿在攻打襄平城对公孙渊也用过。只要给人一线生机,人就不会选择鱼死网破,这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求生欲。同样是这种求生欲,会让人在认为自己没有生机时,迸发出强大的战斗意志,那就是曹操在仓亭用背水阵大破袁绍的故事。
听过那个故事的人应该还有,因为辛毗的儿子辛敞还活着,他此刻的身份是曹爽的参军,他听了姐姐辛宪英的话闯出洛阳追随曹爽,可他和同来的鲁芝说的话却像是司马懿的说客,尽管他对之言听计从的姐姐说过司马懿想要曹爽的命,辛敞仍然认为曹爽回去不会有生命危险。
同样身为曹爽的忠臣,桓范和辛敞、鲁芝的观点截然相反,在曹爽犹豫的时候,司马懿的使者许允、陈泰传达了司马懿“只夺权,不害命”的承诺,但这不足以让曹爽放心,直到殿中校尉尹大目带来了司马懿的誓言和蒋济的书信,曹爽才对洛阳方面有了信任。
因为看到了生路,所以他的死期到了。
司马懿的哄骗大获全功,曹爽放弃了抵抗束手就擒。除了曹爽外,他的亲弟弟曹羲、忠心耿耿的辛敞、鲁芝,也都相信司马懿的目的只是夺权,力主内战的只有桓范一个人。以司马懿那据说在诸葛亮之上的军事水平,曹爽和他打能有几分生机?
投降生机极大,反抗生机极小,那就投降吧。
曹爽并不愚蠢,但是他太怕死了,这个心理弱点干扰了他的判断,让他愿意相信放弃抵抗能够活命。人是一种软弱的动物,为了消除心中的不安愿意相信任何事情。回到洛阳的曹爽被关押在私宅里,他试探性地给司马懿写信要食物,司马懿给了他食物和回信,这让他欣喜若狂,确信自己的命保住了。
司马懿其实是胜券在握,可以从容走完程序再动手。
“然后押曹爽兄弟三人并一干人犯皆斩于市曹,灭其三族。”
演义中此处的叙述非常简单,并未写曹爽最后时刻的绝望和崩溃。演义是一部写强人的书,对弱者的心境殊少同情。曹爽不傻,但是他不够强,强者的比拼是智慧的较量,更是意志的较量,当意志瓦解,智慧就无所凭依。桓范的哀嚎并非骂曹爽愚蠢,而是骂他窝囊,因为桓范拿来对比的,是曹爽的父亲曹真。
曹真并不聪明,但是非常有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