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标签,是诸葛亮们加注的
一、干旱
地方志、私人日记、官员的奏折、口述史资料、外国人的报告等文献资料均表明,始于1899年末的义和团运动的蔓延和强化,与旱灾给人们造成的紧张、忧虑、失业和饥饿有关。

但干旱并不是1900年春夏义和团运动到处蔓延的唯一原因。在特定地区,官府对义和团采取支持(如在山西)或反对(如在山东)的立场,对运动的发展也有着重大影响。不过,旱灾以及它给人们带来的情绪波动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当老天开始下雨,使干旱暂时中断或彻底结束时,义和团员(还有大刀会员)会抛开一切,返回他们的农田。4月初直鲁交界地区“下了一场透雨”后,农民们都忙着回家种庄稼,这些地方随即“平静了下来”。7月4日大雨倾盆,天津的一支义和团被洋人打败后,争相逃命的拳民互相谈论说:“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第二天即散去大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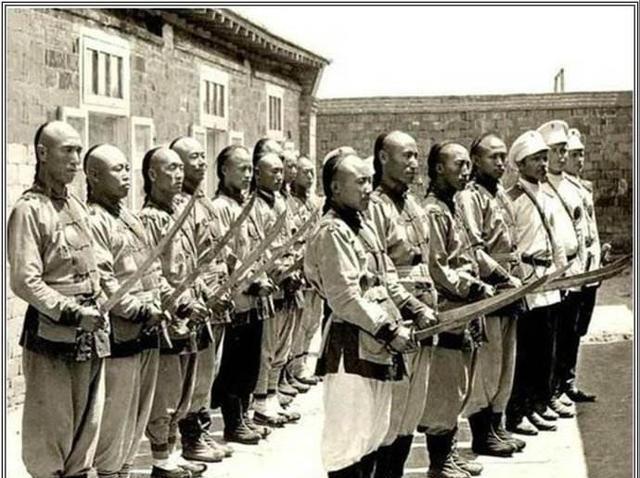
林敦奎对义和团时期自然然灾害的作用进行了专门研究, 他的结论是:“自大刀会初起之时至义和团高潮之际,有不少灾民是以天时好坏作为参加运动的主要动机。
洪涝、干旱这类自然灾害,从古至今都存在,但对干旱成因的解释,从古至今的版本太多了,只有到了近现代自然科学揭示了气候变化原理之后,干旱才变得不再神秘。
二、析因
对事物间的因果逻辑认知,对人的行为有重大影响。同样是干旱,古人认为干旱是因为有人得罪了雨神,要使雨神降雨,除了祭祀求雨别无他法。现代人的做法是,打几炮人工降雨。
当时义和团民对干旱成因的解释是,义和团包括当时非义和团的中国人,把传教士和其他所有洋人看作中国大地上的恶之源,看作引起众神愤怒的直接因素。兹因天主耶稣教,欺神灭圣,忘却人伦,怒恼天地,收住云雨,降下八百万神兵,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期。
当时流行的打油诗:杀了洋鬼头,猛雨往下流。洋人杀尽,欲雨还雨,欲晴叫晴。
难以预测和不可把握的自然灾害,使人们经常遭受饥饿之苦,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把造成饥饿的直接原因(久旱无雨),与人的某些不适当的行为——破坏宇宙平衡的行为,义和团运动时期是洋教的入侵——挂起钩来。
长期以来,此种思维模式深深地印刻在中国人的文化活动中。在许多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其他不同的文化:环境(特别是农业社会)中,这种模式也广为流行。但这种思维模式,不只中国独有,其他国家也非常普遍。人理性有限以及归因谬误,不分人种、国家。
三、行动

面对旱灾,人们首先进行祈祷,举行各种各样的祈雨仪式,但当这些常规的方法一直不奏效。当持续干旱引起的忧虑日益加深时,人们常常会采取更激烈的措施。
常见的做法就是寻找替罪羊,确定哪些人该对危机负责,并对他们加以惩罚。不过,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环境中,抛出替罪羊的方式是大不相同的。
在某些地方,人们指责老年妇女是巫婆,是她们用巫术恶毒地驱散了乌云。1949年,非洲东南部的马拉维发生旱灾,人们把矛头指向头发灰白或秃顶的老年男子,指向制砖工人,因为人们认为这两类人能从干旱中得到好处。当印度西部的吉尔拉特没有下季风雨时,当地的比尔人怀疑是巴亚尔商人故意使坏,造成干旱,以便抬高商品价格,牟取暴利。为打破这个魔咒,比尔人强迫一位巴亚尔人在头上顶着一个水罐子,他们放箭射击,直到罐子破裂,水流满地。
人采取手段实现目的的过程,是渐进式的。解决下雨最优先使用的方法是低成本的祈雨,然后才是高成本的找替罪羊,替罪羊的寻找顺序也是从低成本的老弱病残开始的。
偶发的攻击,也是捡偏僻处、形单影只、妇女儿童下手。经济核算思维从古至今,从蠢货到智者,这一事实、规律从未变过。
四、事后诸葛亮解释
不少历史学家坚持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他们倾向于把起因归结为19世纪末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逼急剧强化。
“反帝”一词被20世纪中国人的政治考量和政治活动,染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帝国主义的确是中国人面临的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是激发义和团运动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
但它仅仅是众多原因之一,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它起的作用是大不相同的。此外,对代表帝国主义的传教士、教民、铁路、电报和外国军队等人和物采取的行动,有可能是由许多动机促成的,并不仅仅是由“爱国主义”或“反帝思想”促成的。因而,把这个词强加于义和团运动,会带来过分简单化的失误,看不到义和团的动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有人的爱国只需点唾沫星子,有人把爱国当成作恶的挡箭牌,他们攻击外来产品、外来思想、外来人物,原因无他,只因太爱国了。
对历史的解释只能回归个体,《没有马云,也一定会有赵云、李云、王云吗?》了解和认识当时人的价值观、思维模式和心理倾向等等,才能更好的解释历史动因。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几年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剧了,但是,对华北平原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而言,与席卷华北的干旱不同,外国势力在1899-1900年并无明显的增长。无论就中国教民社区的扩大,以及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团体的力量的加强来说,还是就铁路和电报的建设,以及外国军队的入侵而言,生活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农村地区的老百姓,在这几年里实际上很少有直接接触这些洋人洋物的机会,即使偶尔有之,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换言之,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中国人与洋人、亲外国的中国人和外国技术,直接接触的机会从总体上讲是增多了。但这些机会在华北的分布并不均衡。
有人认为义和团的行动是其反帝动机促成的,照理帝国主义影响最大的那些地区,应该普遍发生义和团运动。但情况却并不是这样,外国经济活动最兴盛的地区——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显然没有义和团的影子。还有将近一半的传教地区也没有闹义和团。义和团运动与人们认为,引发这场运动的宗教因素及外国侵略因素之间,实际上无太大关系。
从担心和仇恨外来者的方面来说,中国一直存在着排外主义的潜流,但是,只有在外部环境发生动荡,某个社区或地区的力量均衡状态被打破时,这股潜流才能活跃起来。
中国人的排外行动,与17世纪塞勒姆的反巫师活动,和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反犹太人活动颇为相似。就上述事例而言,在“正常的”情况下,外来者在中国是西方人,在塞勒姆是那些被指控为巫师的人,在德国是犹太人,都能在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过相对平静的生活。但是,当某些因素致使环境变得“不正常”,在德国是经济危机,在17世纪末的新英格兰是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的担忧,在世纪之交的华北是对干旱的忧虑的时候,绝望的人们就会想方设法发泄不满,缓解危机,外来者往往首当其冲。
历史不会重演,却总是惊人的相似。之所以相似,是因为行为背后的理念是共通的,1900年人的行为和2024年人的行为的具体排外内容绝不会相同,但行为背后的排外理念是共通的。理念可以穿越历史经久不息的。
除了普遍且剧烈的天灾,像恐龙灭绝时代那样,日子并不会突然难过起来。在没有普遍天灾之下的普遍难过日子,是错误理念不断践行的结果。
有人说依靠现代化的传播工具,正确理念的传播应该很容易。不一定,传播的前提是理解并认可理念。真理和谎言,往往是谎言更容易被认可传播,真理通常是反直觉的,得下一番艰苦思考才能领会,两者在被大众理解和传播的成本上就一分高下了。
“现在网络主要问题,就是信息茧房太严重了。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信息茧房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容易引起傻逼共振,以前可能方圆十公里就一个傻逼,但是现在北京的傻逼,上海的傻逼,广州的傻逼,就可以在一起高山流水遇知音,共振出信息茧房,然后创造出更大的傻逼。” @苏睦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