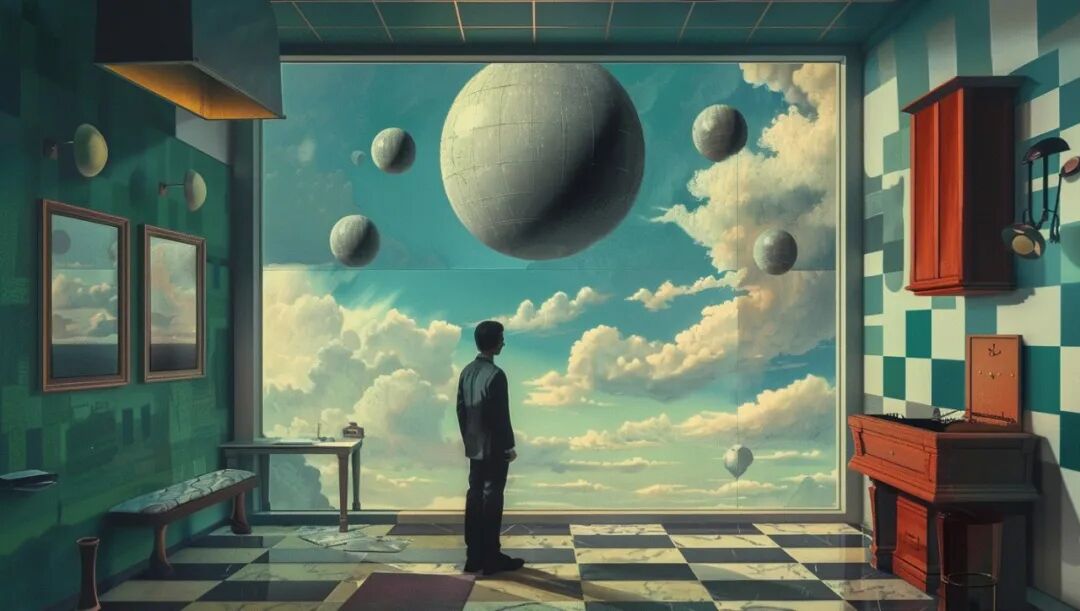谁说A股没有慢牛?罕见持续了18个月!
作者:人神共奋 复盘系列:2016-2017 季线六连涨 这一波行情以来,一直有人说,A股开启了慢牛时代。这话并不准确,就算慢牛时代真的来了,最多也是“再度”开启了慢牛时代。 2016下半年和2017全年也是这样的慢牛行情,这一年半沪深300连涨六个季度,而且涨幅控制在27.8%,18个月中有14个月上涨,只有4个月下跌,月胜率不低于牛市。沪深300历史上只有06-07年出现过9季连涨,但那是大牛市,之前14-15年五季度连续上涨,涨幅最高150%。 这一年半的A股历史上罕见的长期慢牛,特别是2017年,12月中只有2个月下跌,最大月跌幅仅-0.47%,是赚钱效应非常好的一年。 但这个赚钱效应仅仅针对大盘股。 2017年的另一个特点是极致的大票风格。当年的上证指数、深成指,沪深300分别上涨6.56%,8.48%,21.78%,看上去是牛市,但当年个股涨跌幅中位数为-20.4%,相比之下,2022年这种标准熊市,个股中位数才下跌了-18%。 2016~2017年这轮大票风格和慢牛走势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极致大票风格与慢牛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宏观经济的变化 2017年被称为“白马蓝筹复兴元年”,自2009年的4万亿行情后,大盘蓝筹股就一蹶不振,持续多年跑输小票和科技股,就算是经过了小票遭重创的2015年,2016年也是小票略占上风。 所以在2016年下半年大票刚刚跑赢时,投资者并没有想到2017年风格颠覆,完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大小票风格变化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宏观经济方面的,2016-2017年的棚化货币化和供给侧改革推动的一轮经济复苏,并由房地产驱动,造成了大小票业绩的此消彼涨 。 2016年,虽然GDP增速仍然下降,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结束了连续两年下降的趋势,主要供给侧改革淘汰落后产能,如钢铁、煤炭行业,推升了工业品价格。棚化货币化引发的新一轮房价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引发了消费升级,家电、食品饮料行业ROE稳步提升,龙头业绩增长,引发大盘股估值修复。 但供给侧改革对小票业绩影响更偏负面,周期品价格上涨,强化环保政策,中小型企业成本上升,下游的通胀又不明显,挤压了中游制造业的利润,削弱了估值支撑,面临戴维斯双杀,而这一部分又是以中小企业为主。 2016-17年,大部分时间,大企业的PMI都是50荣枯线以上,小企业在50以下。 另一方面,创业板在2014-15年资产重组带来的业绩高增速不可持续,特别是跨行业重组的泡沫破裂,传媒、计算机等TMT行业亏损扩大。 这一分化在财务数据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主板上市公司的利润增速从2016年的5%上升到2017年的20%,而中小板从37%下降至20%,创业板更明显,从2015年的增长55%下降到2016年的增长38%,再变成2017年的下降 -21%。 但2017年的业绩要到2018年4月才全部公布完毕,市场不会等到那个时候再变,而是有了边际变化就开始逐季定价,所以从供给侧改革开始的2016年,大小票的风格转换就开始了。 这两年虽然都是慢牛,但2016年的“慢”大于“牛”,市场成交量小,波动极低,可以看成巨幅波动的2015年的对立面,市场非常乏味,也没有明显的风格,大小盘风格不明显,成长价值风格也不明显,也没有什么板块机会。 2016年只有白酒牛,到了2017年才扩散到更多行业的龙头。 所以,市场风格的变化仍然准确地反映了宏观经济的变化,只不过,当数据还没有统计出来时,更重要的是从自下向上发现变化,再从这些纷繁复杂的变化中找到主线的能力。 当然,比上市公司业绩变化更容易捕捉的,是监管风格的变化,以及资金结构的变化。 监管风格的变化 以前提到这种风格转移,总是把估值当成第一原因。的确,2016年底大市值股票估值处于历史低位,而小市值股在2015年牛市中估值泡沫化。 但估值从来不是风格转换的条件,A股市场的估值弹性极大,高的可以更高,低的可以更低。 A股这种“政策市”,首先要从监管的变化上找原因。 大小盘风格转换,首先源于2016年的监管环境,可谓史上最严,这是2015~2016年三次股灾的后遗症,特别是3.0的熔断事件,实际是一次非常严重的人为事故,导致新上任的监管部门负责人对市场风险管理极度谨慎,规范再融资、收紧并购重组规则,限制壳资源炒作,等等,这些小票炒作的生存土壤都被限制了。 最能体现这一监管环境的是2016年的“宝万股权大战”,这本是一次标准的市场化收购,也是证券市场的功能之一,以往监管部门都是中立的,但本次对收购方“妖精、害人精”的态度鲜明的定性,就是这种风险厌恶情绪的表现。 同时,宏观经济的调控风格也开始转向“去杠杆”,2017年发生对未来金融体系影响重大的是资管新规,虽然真正的“信用收紧”要到2018年,但中小企业在2017年就开始感受到寒意。 这些监管政策中,对市场影响最大的是对游资的打击,连“总舵主”都被抓了判刑,引发了资金结构的变化。 资金的变化 过去在分析2017年慢牛行情的原因,总是归结为外资和公募基金对白马股的推动,但数据对两者的支持程度不同。 2017年的股票类基金和混合型基金虽然净收益亮眼,分别为13.6%和10.7%,但并没有体现在规模上,分别增长4.13%和下跌-1.78%,所以公募基金只是风格转换的受益者,而非推动者。 再看外资,2017年6月,MSCI宣布将纳入A股,但实际是直到2018年才开始,大规模提升占比是2019年的事,但的确存在一部分外资想提前“坐轿子”,加大了净流入力度。 2017年北向资金的净流入1997亿,开通三年历史积累净流入3475亿元,2017年增长明显,当年深股通的净流入金额是沪股通的2倍,所以深成指涨幅迅于上证指数,另外,当时占主导的QFII持仓规模也有明显的增长。 虽然几千亿的增量资金并不足以改变存量资金结构,但新增资金的买入方式却是2017年慢牛的资金方面的根本原因。 2017年的北上交易规则限制还比较严格,此时进入的外资明显是长期配置型风格的long-only资金,采用无视市场的持续买入策略,小跌小买,大跌大买,买入后即锁仓。 深股通当年前11大成交活跃股,去掉万科A后恰好就是深股通年终持有市值的前十,也证明了外资“买入并持有”型策略 A股此前并没有这一类“长期配置型”风格的资金,因此给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先看一看2015-2017年公募基金十大重仓股的变化: 再看一看北上资金2017年12月的前十大持仓,这20只股票占北向资金持股总市值的的59%,2017年平均涨幅高达75.7%。 公募基金2017年的十大持仓与北向资金重仓股的重合度,在2015-2016年不高,但2017年基本重合,明显向外资靠拢。 市场资金规模并没有增长多少,但结构发生了巨变,另一个原因是前面说的对游资的打击,市场流动性大幅下降,流动性是小盘股炒作的前提。 自2002年一系列庄股的崩盘之后,游资炒作就成为A股最主流、最成功的盈利模式,而这一模式的转折点发生在2017年,体现在雄安新区题材炒作的失败上。 2017年4月1日,国家突然宣布设立雄安新区,这种“百年大计”型的题材,A股自然必炒,华夏幸福连续6个一字板,但这次炒作可谓“失败中的失败”,几乎所有的题材股最后都是“A杀”,不但参与炒作的游资和散户大部分被深套,而且还拖累了大盘,4月成为2017年唯二下跌的月份之一。 这是因为。小盘股题材股的炒作高度依赖流动性,所以2016年对游资的打击,对流动性影响极大,失去“流动性”这个炒作的土壤,管你什么世纪题材都炒不起来。 2017雄安题材炒作的失败,让大量游资开始谋求转型,A股进入“游资、公募机构和外资”共同定价的时代,这三种力量的定价能力,以及哪一个成为增量资金的主要来源,成为市场风格变化的决定性因素。 2017年增量资金的天平只是略微倾向外资,风格已经到转到了大盘股这里,大盘股凭借稳健的资产负债表和更低的换手率,更容易对抗流动性下降的风险,而散户资金流出小票,加剧了小市值股的流动性危机。 慢牛的终结 写到这里,先小结一下。 2016-17年的风格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风格从小票切换至大票,二是慢牛。但这两个特征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上面分析的三个原因中: 宏观面的原因导致了大小票风格转换,但大票风格并不一定是慢牛; 慢牛的直接原因是外资配置型long-only风格的影响; 监管的风险厌恶,对游资和小票炒作的打击,对大票风格和慢牛行情都有影响。 对于A股,最难的不是“牛”,而是“慢”,而2017年形成慢牛,有一定的偶然性。 首先是监管很严,限制了炒小炒垃圾炒重组这些容易放大波动率的因素, 其次是资金面不紧不松。 事实上,2017年的流动性环境并不好,M1持续下降,资管新规的压力下,事实上从宽信用向紧信用过渡,但2017年“9号文”减持新规,让市场的减持压力减轻。 2016-17年这六个季度的慢牛,是只属于大盘股的“半个慢牛”,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流动性的约束,靠小票不断下跌的抽血来维持,也让行情能维持在慢牛的状态下。 最后是基本面不坏不好,大票边际向好,小票边际下降,投资者对基本面的分歧也是慢牛的基础。 在大小盘风格转换中,再加上供给侧改革造就的周期股行情,市场的分歧非常大,导致流入大票的资金与逢高兑现的资金形成了“略宽松的平衡”状态,资金净流入的水龙头一直保持细水长流的状态,风险偏好一直在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才是这种慢牛资金上的基础。 但慢牛发展到了2017年底,各种条件都压不住了。 首先是资金层面,股票基金优秀的表现吸引了大量新资金,2018年初,兴全合宜混合发行,市场疯抢,产品最终以327亿元规模成立,成为当时公募基金历史上成立规模第二大的偏股基金。 基本面也压不住了,2017年10月底,茅台公布炸裂的三季报,净利润增速60%,紧接着,三大行的利润增速达超过14%,基本面分歧消失了。 经过长期六个季度的市场教育和实实在在的“大象起舞”的业绩增长,投资者终于接受了大盘蓝筹股估值革命的逻辑,感觉到牛市重新回来了。10月后,资金加速报团白马股,冲上3400点,四季度回落调整了两个月,到了年底,在银行股集体大涨的推动下,终于变疯,冲到3587的年度最高点。 而监管的思维停留在过去,限制炒小炒新,但对于披“蓝筹股价值重估”外衣的炒大票,却是一点办法没有。 非正常的慢牛行情 说A股未来会进入慢牛时代,过去20年,我起码听过3遍,理由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数量变多,规模变大、经济增速更加平稳、机构投资者占主导,监管能力的提升,等等,但这些理由都靠不住。 上市公司数量变多,规模变大,但资金增加更多; 经济增速更加平稳,只能让业绩整体增速更平稳,但估值区间并没有变小,而后者才是波动的主要原因; 机构投资者占比增长并没有比散户更快,而且机构投资者拿到基民的钱,继续买入自己的重仓股,短期内起到压制波动率的效果,形成慢牛假象,但这种抱团到一定时候必须变疯。 至于监管控制能力的提升,慢牛并不是光靠管就能管出来的。 从2017年复盘,可以看到慢牛行情的三个特点: 慢牛行情都是由新资金不断入场引发,喜欢回调买入,造成慢牛 慢牛行情会把某一种风格演绎到极致,所以不要因为涨多了就想换赛道 慢牛行情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散户资金后,难免变疯牛,几次加速-调整-再加速之后,最终波动率放大,以暴跌结束。 慢牛实际上是一种A股的“非正常”状态,是宏观基本面、监管风格、增量资金来源等一系列严格的条件,在偶尔事件推动下的产物,其状态必然不稳定。 人没有记性就会反复失望,所以我对“慢牛”持欢迎但不抱希望的态度。
来源:思想钢印(ID:sxgy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