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妥协的意愿愈发强烈!
作者:印闲生
来源:江宁知府(ID:jiangningzhifu2020)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密切接触。
4月12日,特朗普总统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阿曼重启伊核问题对话,这是自2018年以来双方最高级别的磋商。
或许是考虑到两国舆论的感观,对外宣称是进行“间接会谈”,即由阿曼外交大臣互相传话,类似于中介在买家和卖家之间谈价格。
不过据多家媒体报道,美中东问题特使与伊朗外长进行了简短的直接面对面交谈,且反响良好。
会后,白宫称谈判“非常积极且建设性”,是“朝互利迈出的重要一步”。
伊朗则由外长亲自上国家电视台宣传谈判成果,阿拉格奇表示:
“美方也表示希望尽快达成协议,但这并不容易,需要双方展现诚意与意愿,而今天的会谈使我们在谈判基础上大大接近了共识,双方都不希望这是一场空洞无果、纯粹为了对话而对话,或是旷日持久的谈判。”
作为这场对话的主要决策者,特朗普本人的立场十分清楚,即务必达成伊朗弃核协议,否则将有极大可能性联合以色列实施军事打击。
很多朋友认为,特朗普第一任期主动退出了伊核协议,所以他不可能“自己打自己脸”,第二任期再把伊核协议签回来。
这种判断是不准确的,因为特朗普反对的是民主党签下的伊核协议(以色列和沙特也反对),认为它未能涵盖伊朗的导弹计划和对“抵抗组织”的支持,且限制伊朗核能发展有过期期限。
假如把协议“从严处理”,确保伊朗永远无法拥核,特朗普其实是支持的。

为什么伊核问题突然浮出水面呢?
其中的逻辑不难理解。
前文引述过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观点——伊朗的国家安全战略存在三根支柱。
第一根支柱是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
伊朗拥有可观数量的新型弹道导弹,最远射程能达到2000公里,之前伊朗曾两次使用导弹对以色列本土进行了打击,效果只能说一般,这让其导弹的威胁程度有所下降。
第二根支柱是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伊拉克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叙利亚等组成的抵抗网络。
过去两年里,抵抗组织遭到重创,甚至连伊朗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叙利亚也发生变天,这无疑让伊朗通过代理人来威慑以色列的力度大打折扣。
第三根支柱即核威慑。
既然前两根支柱遭受了严重削弱,那么加速核研发就自然成为伊朗不得已之选择,如此也就触动了美国和以色列最敏感的神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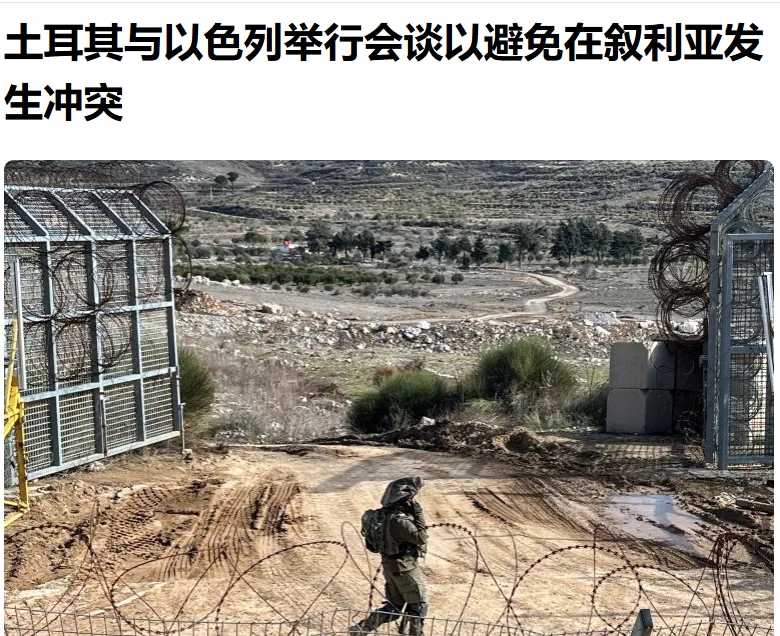
叙利亚新总统谴责伊朗是宗派主义和腐败的根源,叙伊关系大幅下降,曾经是伊朗势力范围的叙利亚如今已成为以色列和土耳其的角逐之地。
在应对伊朗核计划问题上,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近期进行了两次面对面会晤,综合各方面信息做推测,美国和以色列的上中下签大致如下。
美国
上签是达成一份“更严厉的伊核协议”,这样既能保障以色列安全,又能以轻微代价(部分解除对伊朗制裁)维持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
中签是没有达成协议,对伊朗关键核设施采取外科手术式打击,并在整个中东范围内与伊朗展开冷战或小规模冲突——类似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军暗杀苏莱曼尼之后的美伊关系。
下签是伊朗执意拥核,且外科手术式打击不成功,美国被迫卷入一场中等以上规模战争。
以色列
上签即拉着美国打一场针对伊朗的全面战争,一劳永逸解决掉威胁,或者退而求其次,对伊朗境内核设施做外科手术式打击——之所以美国的下签成了以色列的上签,是因为战争的主要成本由美方承担,而战后收益则由以色列享受。
中签即达成一份“更严厉的伊核协议”,考虑到以色列对伊朗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内塔尼亚胡认为“新伊核协议”不过是德黑兰的缓兵之计。
下签是维持现状,假如美国既不同意打击伊朗核设施,又没有达成“新伊核协议”,那么以色列只能单独行动或接受伊朗即将拥核的事实。

民主党时期美方的态度其实就是以色列的下签,特朗普虽然也不同意全面对伊开战,但至少更强硬一些,已经频繁威胁要对伊朗核设施做打击,并以此施压德黑兰接受“新伊核协议”。
视角回到伊朗。
过去两年的中东危机某种意义上是对伊朗“抵抗之弧”战略的一次总检验,然而实际效果只能说差强人意,特别是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意外垮掉,打了德黑兰一个措手不及。
不仅如此,2024年5月 伊朗总统莱希和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在一次直升机失事中丧生,这让德黑兰“强硬派”力量再受重创。
这样的背景下,对美国政策成为伊朗内部争论非常激烈的话题,以新总统佩泽希齐扬为首的“温和派”力量逐渐占据上风,他们支持同美国改善关系,换取华盛顿解除制裁。
对德黑兰而言,当前政权所属的势力范围已经处于历史最弱时期,而且面临着军事压力、严厉制裁、权力交接与经济动荡等一系列问题。
抖音上有位伊朗博主叫“波斯娜菲菲”,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她在伊朗属于妥妥的上流社会,其社交媒体的立场非常正统,但即便如此,从其对日常生活的分享中也能感受到伊朗社会经济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举几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每次坐飞机都心惊胆战(因制裁导致零部件匮乏),进口工业品价格奇高(如私家车),申请欧洲签证屡次被拒(即使缴纳一万欧元押金还是被拒),在伊朗以色列互相报复期间带着家人跑到上海等等。
上流社会尚且如此,普通人可想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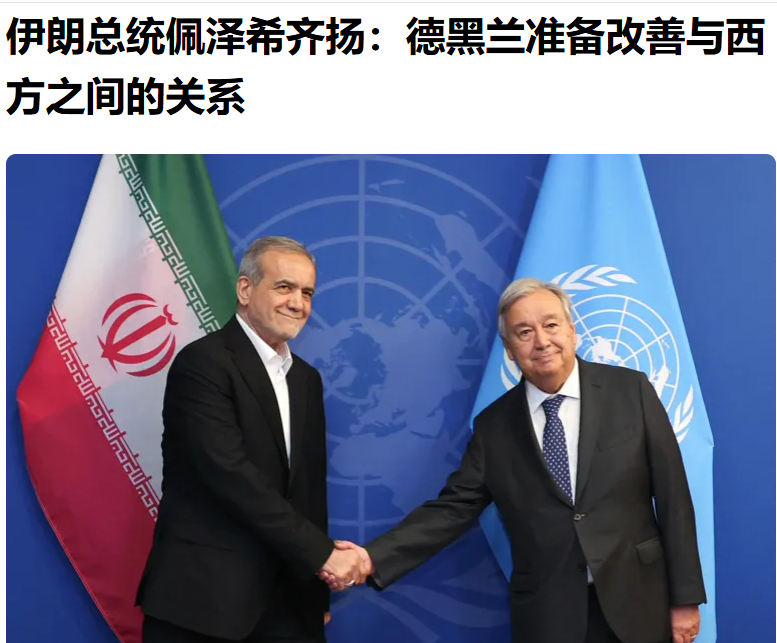
伊朗新总统佩泽希齐扬被视为“温和派”,在联大等场合曾多次向美国试探性喊话,直到近期才获得积极回应。

哈梅内伊(中)为佩泽希齐扬颁发总统任命。3月12日,美国通过阿联酋把特朗普写给哈梅内伊的信转交给伊方,信中措辞强硬,呼吁双方进行直接谈判。
每个古老帝国都有一套根深蒂固的世界观,伊朗也不例外。
历史上,以伊朗高原为基础建立的帝国往往横跨两河平原至中亚的广大地区——类似于“扁担挑两头”,中间的伊朗高原是那个“扁担”。
随着近现代以来列强崛起,伊朗高原以西至地中海的广大地区被英法等海洋列强瓜分,高原西北的高加索一带被割让给了俄国,高原以东至中亚土库曼斯坦、阿富汗一带的势力范围也被俄国占领,东南方向的南亚次大陆则沦为英国殖民地……
要不是地形因素导致深入内陆统治成本过高,伊朗早就被列强吃抹干净了。
1925年成立的巴列维王朝是对恺加王朝的一次政变,并没有改变伊朗受制于列强的本质,实际上,在1979年之前,德黑兰统治者始终战战兢兢地寻求列强庇护,以维持自身脆弱的统治。
1979年伊斯兰革命是近现代以来伊朗历史的转折点,它极大激发了伊朗的民族主义思潮。
此后伊朗在强大教权的凝聚下变得愈发“积极进取”——站在波斯人视角,有一点民族复兴的意味。

伊朗计划和在建的七条新线路。伊朗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在南北走廊中连接印度和俄罗斯,在东西走廊中连接亚洲和欧洲,同时还是中亚出海最方便的通道。
战争是重塑地区力量格局最激烈的手段,也是促使一国进行战略调整最迅速的方式。
经过过去一年多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对抗,伊朗逐渐意识到自身实力的局限性,现阶段有进行战略收缩的倾向。
犹记得2005至2013年内贾德担任伊朗总统期间,他经常宣称“我向真主发誓,永远不会去了解经济学”——以此表示自己坚决反美不计代价。
然而到了2024年竞选总统时(最终被哈梅内伊排除在外),连内贾德都公开表示自己最大的参选动机是改善国家经济形势。
事实上,以美元计算的伊朗GDP只剩下4035亿美元,远未恢复到2008至2017年的水平,比2011年的高峰少了35%。
如果考虑到2018年之后伊朗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严重背离,以美元计算的伊朗GDP规模还要进一步大幅度缩小。
再跟周边海湾阿拉伯国家一对比,同样盛产石油,海湾国家的人均GDP五倍、十倍于伊朗。
这种情况下,德黑兰有思变的情绪也就不难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