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撤退!
作者:印闲生
来源:江宁知府(ID:jiangningzhifu2020)
历史上,美国全球霸权崛起的过程大致为“美洲→欧洲→日韩→中东→东南亚”,正常情况来说,有朝一日霸权瓦解顺序将倒过来,即“东南亚→中东→日韩→欧洲→美洲”。

六七十年代打越战时,曾有几十万美军常驻东南亚,现如今早已撤得精光。
很多朋友可能不清楚,冷战期间在建立起北约之后,美国也曾搞过一个“东南亚条约组织”,即SEATO,简称东约。
东约就是亚洲的北约,总部位于泰国曼谷,它有八个成员国,分别为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以及三个受保护国——南越、老挝和柬埔寨(1956年后拒绝接受东约的保护)。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虽然没有加入东约,但事实上共享了各种情报信息。
东约存在了二十二年,1975年南越的灭亡给了其致命一击,标志着该军事组织已无法保障成员国安全。
随着越战结束后美军陆续撤离该地区,多个东约成员国表示无意继续参与,东约遂于1977年6月30日解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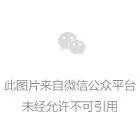
1966年菲律宾马尼拉东约会议的场面
东南亚之后,美国第二块有战略撤退倾向的地区是中东。
1990年代,美国在欧洲的大量军事资产陷入无事可做的境地,拔剑四顾,华盛顿决定把一些驻欧洲的部队逐步调到距离不远的中东,并连着打了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三场大战。
关于这三场战争背后的战略意图可谓众说纷纭,有的解释为美国想进军亚欧大陆腹地,有的解释为控制中东能源,还有的说就是为了反恐……
不过时至今日这些已经不重要,因为美国已经很大程度上从中东撤军,只留下一堆基地和留守人员作为框架,以方便万一有事时好迅速补充进来。
现阶段美国对于中东事务更多是出于“应付”的态度,被以色列推着跑——这一点在拜登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即尽可能平息事态,不愿意投入太多资源。
实际上,过去两年多里要不是以色列这个代理人战斗力比较强,咬着牙跟“抵抗轴心”打到底,美国的中东战略可能早就崩溃了,华盛顿并没有决心派重兵去跟伊朗及其代理人打一仗。
说来也是运气,2024年下半年“抵抗组织”接连发生低级失利,特别是叙利亚变天,让美国和以色列信心大增。
德黑兰方面感受到很大压力,进而将伊核问题加速推上台面,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国际原子能机构称,伊朗近期增加浓缩铀的生产,已接近制造原子弹所需的90%。
进入4月以来,中东局势暗流涌动。
在美国和伊朗正式启动核问题谈判的同时,美军又向中东地区增遣了一个航母战斗群,达到双航母战斗群的准战时配置,外加将B-2隐形轰炸机也部署到迭戈加西亚基地。
接下来如何决断,对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将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如文章一开始所说,正常情况下美国战略撤退顺序是“东南亚→中东→日韩→欧洲→美洲”,不过实际情况并没有按照常理,因为美国把亚太地区的重要性摆得高过了欧洲。
出于跟中国战略竞争的迫切需要,目前美国更倾向于从欧洲抽调军事资源来增强亚太。
从特朗普近期的动作来看,他在乌克兰问题上减少投入的意志是非常坚决的,而且这种转向的背后有着庞大民意基础做支撑。
为什么美国民主党、德国社民党、英国保守党以及法国马克龙政府在过去一年的选举中均遭受重大挫败呢?
原因当然是内部社会经济问题,但反映到外交领域,越是内部形势不景气时,民众对于政府长期对外援助就越持负面态度。
或许每年援乌的几百亿美元对美国来说确实不算什么,可它呈现出的意义是拜登政府把乌克兰摆到解决国内问题之前,并为对手提供了绝佳的攻击靶子——任何地方出现问题,共和党都会攻击拜登总是优先考虑国外而不是国内。
同样的话术也出现在许多欧洲国家。
美国人以“上帝选民”自居,认为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独特作用是命中注定的,被上帝赋予了这个权利。
当连美国人都厌倦对外干预时,说明国际政治的转型已迫在眉睫,未来很可能变得区域集团化。

丘吉尔与戴高乐。戴高乐曾经预言“有一天美国将离开旧大陆欧洲”,随着特朗普的乌克兰政策日渐清晰,不少人认为这一预言正在成真。
文章后半段,谈两个重要的新闻事件。
1、
4月份,德国候任总理默茨领导的保守派联盟与中左翼社会民主党达成联合执政协议,预计新政府将于5月6日起正式执政。
为什么这件事很重要呢?
犹记得十几年前,欧盟委员会主席这个岗位并没有那样显赫,更像是一个执行和协调的角色,当时欧盟的主心骨普遍被认为是“德国总理+法国总统”。
而最近几年冯德莱恩的存在感越来越强,已经隐隐有“欧洲总理”的感觉,其实不是因为冯德莱恩强,是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的影响力变弱了,整个欧盟越来越像一盘散沙。
欧盟给人的印象就是不停地开会,今天一个欧洲峰会在英国,明天一个欧洲峰会在法国,后天再回到布鲁塞尔开。
由于二十七个成员国利益不同,各怀鬼胎,使得重大决策每每难产,声明和宣言发了很多,真正落实下去的政策却很少。

欧盟想要有主见,前提条件是欧盟内部第一大国德国必须得有主见,而德国有主见的前提是组建“大联合政府”。
在德国政坛,基民盟和社民党是传统上最强的两大政治力量(本次大选中社民党屈居第三,被迅速崛起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超越),它们联合执政是德国政治稳定运作的基础,即默克尔时期的模式。
过去几年里,德国采用了罕见的“红绿灯”组阁方式——社民党拉了两个理念迥异的小党一起执政,搞得令出多门,鸡飞狗跳,总理朔尔茨的权威极大受损。
如今中右翼的基民盟和中左翼的社民党强强联合,德国政治的稳定将陡然提升。
其中,候任总理默茨对美立场相对强硬,曾批评美国是“不可靠的盟友”。
在完成组阁谈判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默茨称“德国正在迎来一个强大而有效的政府”,并直接用英语向白宫喊话——“给特朗普的关键信息是德国已经重回正轨。”

德国新一届联邦议院3月25日成立并召开全体会议,朔尔茨总理的任期随之结束。图为朔尔茨在会场从候任总理基民盟领袖默茨面前走过,神态略显落寞。
2、
4月11日,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欧盟与中国已就“设定中国产电动车最低价格”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将以此作为先前惩罚性关税的替代方案。
与此同时,有港媒引述五名知情人士称,欧盟领导人计划7月底前往北京,与中国举行峰会。
如果说拜登时期欧洲认为跨大西洋沟通更加便捷有效,那么随着特朗普归来,在白宫反复碰壁的欧洲领导人最终将意识到,欧盟对中国的影响力将成为它撬动跨大西洋关系的最后一根杠杆。
但北京其实比华盛顿更容易打交道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