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义务帮工后酒驾撞车身亡,家属向工友索赔40万,北京法院判了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乐于助人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随着时代的进步,道德和法律之间开始裹挟着人性的矛盾,“扶与不扶”“救与不救”都成了引人争议的话题。
可刘大叔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送与不送”也把他推到了法律的风口浪尖,且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刘大叔是北京房山人,有着北方老爷们的豪爽和热情,也是古道热肠的一个人,经常给工友们帮忙,因此人缘不错。

2017年4月的一天,他家里进行翻修,要加工彩钢屋顶,工友们听说了,都提出要给他义务帮工,其中就包括了工友老王。
一行人忙活了一上午,刘大叔觉得过意不去,就留他们在家里吃午饭。这群干活麻利的大老爷们平时就爱喝点小酒,为了犒劳工友们,刘大叔也在席间准备了不少酒。
期间老王喝了不少,不过他酒量好,走路尚且稳当,说话也还清楚,他住在邻村,走回去得个把小时,如果一路慢悠悠地走,也没什么大问题。问题就出在,他是骑摩托来的,想要骑着摩托回去。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即便是骑摩托车,在喝了酒的情况下,也是具有高危险性的。所以刘大叔一直劝他在自己家多休息会儿,散散酒意再离开。

不过老王对自己的酒量和摩托车技术相当有自信,直言:“就二十来分钟,我开慢点完全没问题的。”刘大叔知道他的执拗性子,劝了几句后,也就放弃了,只嘱咐他路上小心。
结果老王在行驶到村口时,撞在了道路西侧树上,有过路的人看到打了急救电话,遗憾的是,他没能被抢救回来。老王的家属得知后,悲痛欲绝,明明是好心出去帮忙,怎么回来就变成了冰冷的尸体了?
老王家属气不过,把刘大叔告上了法庭,他们认为若是刘大叔阻止他酒后驾驶摩托,或是采取其他方式送他回家,就不会酿成这样的悲剧,因此向刘大叔索要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40万元。
刘大叔接到法院的传票后,觉得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他辩解道:“我明明也劝了老王,但是老王不听我有什么办法,难道我要把他绑在家里不让他走?”

这话听起来似乎也有些道理,但在法律上他的“无奈”能得到支持吗?法院又会如何判决?
首先老王作为拥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知道酒后驾车是法律禁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第九十一条明确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其机动车驾驶证,终身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摩托车属于小型机动车,也应该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他明知道酒后驾车存在安全风险,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却不顾劝阻,我行我素,因此老王自身存在重大过错。
而且老王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行驶时也没有戴安全头盔,所驾驶的摩托车未按规定登记,还悬挂其他车辆的车牌,存在多项违法行为,加重了自身的安全风险,有扩大有过错的情节。

所以老王要为自己的死亡结果负绝大部分责任,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刘大叔就毫无责任了呢?
当然不是。刘大叔作为饭局的组织者和同饮者,应该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法律规定,在共同饮酒过程中存在以下情节,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1.明知对方不能喝酒,如明知对方的身体状况,仍劝其饮酒诱发疾病。
2.酒后驾车未劝阻导致发生车祸等损害的。
刘大叔明知老王骑摩托车来,不合适饮酒,但没有在席间进行劝阻,反而热情邀请他畅饮,留下了安全隐患。同时知道老王要酒后驾车离开,刘大叔虽然进行了言语上的劝说,但并未有效阻止。

在言语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刘大叔可以选择着人送他回家,或是通知其家属来接,避免出现安全问题,但刘大叔没有采取这些措施,因此老王的死亡结果和刘大叔的不作为存在因果关系,有一定过错。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综上所述,法院认为刘大叔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需要为老王的死承担部分责任,根据刘大叔的过错程度、经济能力等因素,最后北京法院判决刘大叔赔偿老王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98487.7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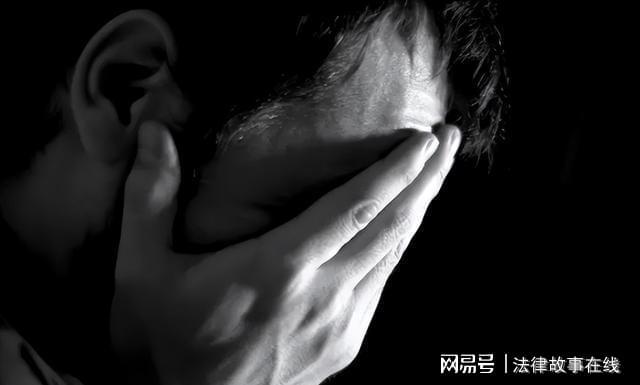
“美酒惹人醉,车祸亲人泪。”醉酒驾驶既是对自己安全的不负责,也是对道路安全的隐患,就如同老王,本是好心去帮忙,结果把工友拖累,也让家人心碎,可见遵纪守法,严于律己,才是避免不幸的良方。














